一份《決議》的誕生是不容易的……
歐洲金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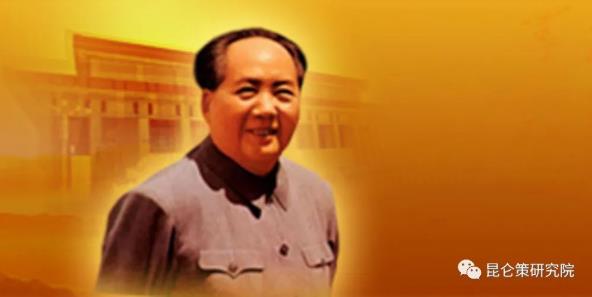
1
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正式通過《關(guān)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這是黨史上的第一份針對史實(shí)記述與人物評論�����,做出自我定論的決議��;也是我們黨第一次對黨史經(jīng)驗(yàn)作出系統(tǒng)總結(jié)��,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要?dú)v史文獻(xiàn)。
《45決議》總結(jié)了黨從1921年成立到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這一時期��、特別是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至1935年遵義會議這一時期�,正反兩方面的斗爭經(jīng)驗(yàn)。
尤其��,《決議》對中央的領(lǐng)導(dǎo)路線問題作了蓋棺定論的總結(jié)��。
這份《45決議》最重要的一個政治成果��、也是歷史成果����,就是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nèi)容,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運(yùn)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xiàn)���。
《決議》在第一段就鮮明地指出:“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自己的領(lǐng)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chǎn)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xué)理論����,創(chuàng)造地應(yīng)用于中國這樣的以農(nóng)民為主要群眾、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wù)而又地廣人眾��、情況極復(fù)雜����、斗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
《決議》在最后又滿懷信心地指出:“二十四年來,中國革命的實(shí)踐證明了并且還在證明著��,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我們黨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斗方向是完全正確的�。”
這份對毛主席領(lǐng)導(dǎo)地位和理論正確的絕對自信,宛如一道石破天驚的長虹貫穿整個黨史����,直到今天依舊光耀東方。
自這份《45決議》為立����,沒有任何人�、任何勢力可以去推翻毛主席在我們黨百年歷史中無可爭議的領(lǐng)袖位置�。
不論是逝去的毛主席本人,還是永遠(yuǎn)活著的毛澤東思想����,以1945這份《決議》為奠基,毛主席于史冊中的形象正式被具象化����。
結(jié)合當(dāng)時的歷史背景,《45決議》中的話術(shù)�,絕不是一般的口號,而是全黨全軍發(fā)自內(nèi)心的共識���。
《決議》從1941年醞釀到1945年最后通過�����,前后歷時四年多的時間����,貫穿了延安整風(fēng)的全過程����,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理解為是延安整風(fēng)運(yùn)動的一個偉大產(chǎn)物�。
因而�����,談《45決議》就不得不談延安整風(fēng)����。
2
1941年10月13日,當(dāng)時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組織“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由毛主席、稼樣同志��、弼時同志���、康生同志、彭真同志五人組成��。
委員會以毛主席為首�����,委托稼祥同志起草文件��,文件名稱為《關(guān)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委員會領(lǐng)導(dǎo)路線的結(jié)論》(草案)。
但是�,正是由于當(dāng)時全黨還沒有開始整風(fēng),黨的高中級干部還沒有集中學(xué)習(xí)和研究總結(jié)過去中央領(lǐng)導(dǎo)路線的是非問題�,認(rèn)識上還有相當(dāng)?shù)木窒扌浴?/span>
可以看到,今年以來隨著《覺醒年代》等黨史劇的熱播�,1921年“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在輿論界講得非常多��、宣傳力度也不可謂不大�����。
但是縱觀《45決議》誕生之前的黨���,這個從一開始就被黨員��、也是被時代所要求“代表著最廣大工農(nóng)階級利益”的黨���,其真正邁向成熟、割除所有錯誤路線在肌體上留下的傷痕記憶的��,正是延安整風(fēng)運(yùn)動����。
甚至可以說��,所謂“建黨”�,這個黨真正被建成也是到了延安整風(fēng)的成功洗禮�����、到了自1935年毛澤東被確定為核心后近十年���,這個人民政黨�����、無產(chǎn)階級政黨其成熟性和底色度均被“刷新”����,才算真正的落定��。
整風(fēng)開展之前��,彼時黨內(nèi)教條主義故態(tài)復(fù)萌���,廣大黨員干部思想認(rèn)識不統(tǒng)一,在軍事和政策上(例如群眾運(yùn)動���、減租減息)�,許多地方都思路不一致。
1935年的遵義會議雖然結(jié)束了“左”傾錯誤的統(tǒng)治�,但并沒有作思想上的徹底清算 。
1937年11月 ��,王明從莫斯科回國后����,憑借手握共產(chǎn)國際指示這道“圣旨”,不僅在組織上�、而且在思想上給黨造成嚴(yán)重混亂 。
客觀來說��,教條主義一直在黨內(nèi)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chǔ)���,直到今天都很難根除����。
那一階段����,許多人把蘇共經(jīng)驗(yàn)和共產(chǎn)國際的強(qiáng)硬指示奉為金科玉律,照搬照抄�。
盡管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已經(jīng)提出許多真知灼見��,但由于教條主義的干擾����,并沒有被普遍認(rèn)可�����,甚至有人譏諷“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
相反,王明以“天子門生”自居�����,自認(rèn)在黨內(nèi)理論地位很高����,危害極大。
從1932年末至1938年夏�,毛主席曾自稱“在這段時間鬼都不上門”,這充分說明了王明在當(dāng)時仍具有很強(qiáng)的影響力���。
而延安之外�,國民黨反動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八路軍����、新四軍被蔣氏集團(tuán)誣為“新式軍閥”���,我根據(jù)地被傳為“變相割據(jù)”�����。
也是在那時���,1943年5月,共產(chǎn)國際被解散的消息傳至國內(nèi)��,旋即“馬列主義已經(jīng)破產(chǎn)”“共產(chǎn)主義不適用中國”“解散共產(chǎn)黨”“取消陜北特區(qū)”等反共輿論甚囂塵上……
如果沒有這么一場延安整風(fēng)�,組織意識和核心意識就不可能重新深入全黨人心——而這兩個意識是造就“毛澤東思想戰(zhàn)無不勝”最重要的政治基礎(chǔ)。
通過延安整風(fēng)與同時期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解放區(qū)的各級機(jī)構(gòu)、軍隊(duì)各層戰(zhàn)士開始更加系統(tǒng)性地認(rèn)識到自己作為革命的一員是在為誰而戰(zhàn)�����,以及如果在革命中陷入迷茫時,應(yīng)該去向誰尋求答案���。
延安整風(fēng)之后����,當(dāng)毛主席的人民領(lǐng)袖地位被進(jìn)一步深化時�,黨領(lǐng)導(dǎo)的革命事業(yè)勢如破竹:從武漢會戰(zhàn)之后至1943年中,日寇軍隊(duì)只對“正面戰(zhàn)場”的國軍只進(jìn)行了一些有限規(guī)模的進(jìn)攻����,而用于對敵后戰(zhàn)場作戰(zhàn)(五次大規(guī)模掃蕩)的兵力,則分別達(dá)到54萬人����、47萬人、46萬人�����、33.2萬人�����、35萬人。
毛主席指揮的的敵后戰(zhàn)場�����,抗擊日軍(不包含關(guān)東軍)的比例分別為62%���、58%、75%��、63%�����、58%�。
僅1941、1942兩年�����,日軍使用千人以上���、萬人以下兵力對我敵后抗日根據(jù)地進(jìn)行的“掃蕩”就達(dá)到132次��,使用萬人以上至七萬人兵力進(jìn)行的“掃蕩”達(dá)到27次����。
通過延安整風(fēng),黨領(lǐng)導(dǎo)的敵后作戰(zhàn)趨于成熟�����,凝聚起了越來越廣泛的群眾力量和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
沒有延安整風(fēng)的勝利��,就不會有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也就不會有《45決議》的問世���。
但是很顯然�����,今天的文藝界和資本圈對延安整風(fēng)并沒有多少投資興趣��。借著黨慶的熱度����,都一窩蜂地把視角轉(zhuǎn)入1921年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這應(yīng)當(dāng)看做是一種遺憾�����。
3
對黨史的研究其實(shí)在黨成立以后不久便開始了�����,包括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鄧中夏等人�,都曾經(jīng)從不同角度對黨的早期歷史作過很有價值的探討和研究。
不過總體而言����,抗戰(zhàn)以前對黨史的研究還處在自發(fā)的、孤立的、零星的狀態(tài)�,缺乏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
作為鮮明的對比����,《45決議》起草的過程,以及六屆七中全會會議的過程����,則是在毛主席的領(lǐng)導(dǎo)主持下,我們黨對自己的歷史第一次進(jìn)行了體系性���、縱向式的總結(jié)和反思���。
從以陳獨(dú)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到成功“糾右”卻又容許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傾向的八七會議���;從1930年5月蔣馮閻大戰(zhàn)的刺激下再次發(fā)作的“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到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代表的新“左”傾機(jī)會主義路線在中央領(lǐng)導(dǎo)機(jī)關(guān)內(nèi)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
正是在這個不斷深入認(rèn)知的過程中��,40年代初的延安����,全黨對于毛澤東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領(lǐng)袖地位����,逐步在討論、研究�、辨析中取得了高度一致的共識。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央機(jī)構(gòu)調(diào)整及精簡決定》���,決定推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給予毛澤東在整個黨的工作中一切重大問題的最終決定權(quán)���。
如是��,毛主席不但在實(shí)際上����、且在名義上成了黨的最高領(lǐng)袖,全黨終于形成了堅(jiān)定維護(hù)毛澤東同志核心和領(lǐng)袖地位的共同意志����。
這份意志,與《45決議》是相輔相成��、相持共生的��。
1942年時�����,少奇同志指出:“黨已有了經(jīng)過長期鍛煉的堅(jiān)強(qiáng)干部��,也有正確的政治路線���,更有了精通馬列主義和中國實(shí)際情況為每一個黨員所擁護(hù)的黨的領(lǐng)袖——毛澤東同志����。”
1943年����,在延安整風(fēng)期間的一次政治局會議的發(fā)言中,恩來同志又語:“經(jīng)過這幾年的實(shí)踐���,對毛澤東的領(lǐng)導(dǎo)確實(shí)心悅誠服地信服���。”
當(dāng)年10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朱老總在講到自己在黨領(lǐng)導(dǎo)下革命二十年的經(jīng)歷時也說:“實(shí)踐證明,有毛主席領(lǐng)導(dǎo)��,各方面都有發(fā)展����;照毛主席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我們這次學(xué)習(xí),就要每人學(xué)一套本事�����,主要學(xué)好毛主席辦事的本事�。”
弼時同志當(dāng)時也說:“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國后�����,我閱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新民主主義論》���、《論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又看到毛澤東在處理國共關(guān)系�����、領(lǐng)導(dǎo)整風(fēng)運(yùn)動以及對各種政策之掌握�����,我認(rèn)識到他一貫正確是由于堅(jiān)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
作為參作人之一�����,聞天同志在《45決議》的修改過程中����,曾在末尾加了這樣一段話:“大會欣幸的指出:黨經(jīng)過了自己的一切成功與失敗����,終于在毛澤東同志領(lǐng)導(dǎo)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組織上第一次達(dá)到了這樣的一致與團(tuán)結(jié)!這是要勝利的黨���,是任何力量不能戰(zhàn)勝的黨����!”
需要看到���,聞天同志自己是親身經(jīng)歷過“左”傾路線錯誤領(lǐng)導(dǎo)的���,還一度在黨內(nèi)負(fù)了“總責(zé)”���,他的這段話可以說尤其具有代表性�,反映了黨在經(jīng)歷了一系列成功與失敗后形成了一股共識。
正是有了這樣的共識�����,也才能自1935年毛澤東被確立為核心后��,我們的中央能夠在偏遠(yuǎn)貧瘠的陜甘寧邊區(qū)一不發(fā)錢�����、二不發(fā)槍�、三不發(fā)糧,就靠著滴滴答答的電報����,指揮黨在全國的組織和武裝;能夠“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變化�,無有留難”;能夠始終保持一錘定音的權(quán)威。
領(lǐng)袖的核心地位�����,一定是需要一份《決議》來維護(hù)的����;而一份《決議》其權(quán)威性的眾望所歸,亦是需要領(lǐng)袖的黨內(nèi)核心地位予以奠定�����。
4
在《45決議》的起草過程中�����,參與的干部們進(jìn)行了多次討論甚至動靜極大的爭吵��,對于諸多歷史細(xì)節(jié)的定義����、歷史事件的評價,黃土之上辯聲不斷����。
其時���,毛主席先后在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中央黨校等不同場合��,做了不同范圍的細(xì)致說服教育工作��,親自找有關(guān)同志深入談話����,為的就是化解黨內(nèi)隔閡,為產(chǎn)出《決議》凝聚共識��。
連《關(guān)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名字��,都經(jīng)過前前后后七次修改����。
如毛主席所言:“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jīng)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
1944年5月�����,弼時同志依據(jù)毛主席三年前起草的《關(guān)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lǐng)導(dǎo)路線問題結(jié)論草案》和“九月會議”的討論�,寫出了草案初稿,題目為《檢討關(guān)于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lǐng)導(dǎo)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全文9000多字。
稿子寫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員征求意見,并由政治局秘書喬木同志作了較大修改�����,后弼時同志又在修改稿上作過三次修改���,題目改為《關(guān)于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lǐng)導(dǎo)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
改來改去�,訂來修去,但決議準(zhǔn)備委員會和七中全會的代表同志們���,仍對稿子不滿意。
對此����,中央便指定聞天同志參加修改。
遵義會議以后���,聞天同志一直在中央負(fù)總責(zé)��,對王明先是“左”傾盲動后是右傾投降的路線變化�����,認(rèn)識比較深刻����。
他隨后在弼時同志的修改稿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四中全會以后的一系列事實(shí)����,形成了比較嚴(yán)密的文字�����,基本上把《決議》的大思路和格局給理出來了��。
1945年春天�,毛主席又在1.3萬字的聞天同志的修改稿的“抄清件”上,親自動手改了七次之多���。
到1945年三四月間進(jìn)入加緊階段后�,高崗?fù)?���、富春同志、劍英同志���、榮臻同志�����、伯承同志�����、陳毅同志�����、朱瑞同志���、林楓同志等負(fù)責(zé)的各個組連續(xù)開會,夜以繼日�����,字斟句酌�。
而所有討論中提出的重要意見,都會及時向毛主席匯報����。
黨中央、毛主席和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zhǔn)備委員會�,會認(rèn)真地研究所有意見,將合理的有益的意見盡量吸收在《決議》中�����。
第一次修改中,是毛主席將題目第一次確定為《關(guān)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并在結(jié)尾部分加寫了:“團(tuán)結(jié)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jiān)固的鋼鐵一樣”這段溫暖又堅(jiān)定的話��。
在第二次修改中��,毛主席又頂著壓力�����、力排眾議對曾受“左”傾路線打擊迫害的同志進(jìn)行了書面的平反昭雪����,還對遵義會議的意義等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補(bǔ)充 。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團(tuán)結(jié)而平反��,為同志去污濁����,老人家的仁心真的從來就是刻在骨子里的。
在一年前1944年的春夏之交時��,毛主席就分別在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和中央黨校作了《學(xué)習(xí)問題和時局問題》的報告(即《學(xué)習(xí)和時局》一文)����,進(jìn)一步闡述了經(jīng)政治局通過的意見。
他明確指出:“不應(yīng)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zé)任方面���,而應(yīng)著重于當(dāng)時環(huán)境的分析���,當(dāng)時錯誤的內(nèi)容,當(dāng)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shí)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dá)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tuán)結(jié)同志這樣兩個目的�����。”
主席對于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tài)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也是我們的黨興旺發(fā)達(dá)的標(biāo)志之一�����。
5
在對《決議》稿件進(jìn)行第二次修改時�,毛主席寫了一段批語:“弼時同志:請邀周、朱���、洛����、劉看一下��,是否這樣改���,然后印若干份��,編號發(fā)給40多個同志��,再集他們座談一次��,就可定議��,再交七中全會通過��。”
《45決議》的起草���,充分發(fā)揚(yáng)了黨內(nèi)民主,是全黨同志共同努力的結(jié)晶����,也是激辯雄論之后誕生的集體果實(shí)。
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開幕的預(yù)備會議上談到《決議》時說:“我們現(xiàn)在學(xué)會了謹(jǐn)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jīng)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沒有大家提意見,我一個人就寫不出這樣完備的文件�����。”
歷史事實(shí)和檔案材料明確無誤地表明�,這其中貢獻(xiàn)最大的始終是毛主席。
是毛主席���,在一眾筆桿子的激蕩辯論中把握著歷史唯物主義的主基調(diào)�����,將黨和紅軍在轉(zhuǎn)危為安過程中的命運(yùn)刻畫����,在白字黑紙上精準(zhǔn)描摹�����;也是毛主席�����,重塑了黨和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對于歷史和未來的準(zhǔn)確判斷���。
即便是在三十五年后的1980年����,當(dāng)小平同志在主持組織《關(guān)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份新的歷史決議——的起草班子時���,也必須向新一批手握筆桿子的同志們鄭重承認(rèn)并嚴(yán)正強(qiáng)調(diào):
“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jiān)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
“我們黨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們贏得了革命戰(zhàn)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從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領(lǐng)導(dǎo)�����,到六屆七中全會提出‘全黨已經(jīng)空前一致地認(rèn)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其間整整十年吶��!”
與之極為雷同的局面是���,《81決議》這黨史淬生于80年代初的第二份黨史決議的起草過程����,同樣如近四十年前的延安��,激辯不斷�����,派論不休�����。
1981年5月,小平同志曾感慨:“這個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經(jīng)過不曉得多少稿。1980年10月����,有四千人討論,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見�;在四千人討論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討論的基礎(chǔ)上,又進(jìn)行修改����,反復(fù)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幾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現(xiàn)在才拿出這么一個稿子來。”
………………
一份《決議》的誕生是不容易的�����。
它關(guān)乎我們會怎樣看待自己走過的路,又涉及我們將如何判斷對不遠(yuǎn)的未來�����。
更重要的是�����,它誕生于六中全會——幾乎歷屆六中全會都會出產(chǎn)重要的政論性文件:
1986年十二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guān)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shè)指導(dǎo)方針的決議》���;
1990年十三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guān)于加強(qiáng)黨同人民群眾聯(lián)系的決定》;
1996年十四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guān)于加強(qiáng)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shè)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
2001年十五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guān)于加強(qiáng)和改進(jìn)黨的作風(fēng)建設(shè)的決定》����;
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guān)于構(gòu)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2011年十七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guān)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2016年十八屆六中全會:《關(guān)于新形勢下黨內(nèi)政治生活的若干準(zhǔn)則》和《中國共產(chǎn)黨黨內(nèi)監(jiān)督條例》。
其最鮮明的作用�,就是為不久后到來的全黨大會做足政治蓄力���。
如四十年前的《81決議》,便為次年中共十二大的順利召開����、承接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打下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回想1945年夏天����,伴隨著《45決議》不可撼動的定力,舉世矚目的中共七大召開����,大會正式選出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新領(lǐng)導(dǎo)班子,同時毛澤東同志當(dāng)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也被寫入《黨章》�。
至此,毛主席在黨內(nèi)的領(lǐng)袖地位得到了進(jìn)一步鞏固�����。
從事實(shí)來看,毛主席在黨內(nèi)「核心」位置的夯立�,也為此后祖國統(tǒng)一、終止分裂割據(jù)局面��、解放全體中華民族的三年解放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起到了難以估量的指揮作用�。
跋
列寧曾這樣表述革命政黨的領(lǐng)袖:“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善于組織運(yùn)動和領(lǐng)導(dǎo)運(yùn)動的‘政治領(lǐng)袖和先進(jìn)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tǒng)治地位���。”
一百多年來的歷史也證明了列寧的預(yù)見�����,工人階級政黨在領(lǐng)導(dǎo)人民進(jìn)行斗爭中����,始終需要一個堅(jiān)持并不斷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善于組織運(yùn)動和領(lǐng)導(dǎo)運(yùn)動的「領(lǐng)袖」�。